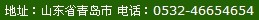|
余秋雨《唐诗几男子》 一 生为中国人,一辈子要承受数不尽的苦恼、愤怒和无聊。但是,有几个因素使我不忍离开,甚至愿意下辈子还投生中国。 其中一个,就是唐诗。 这种说法可能得不到太多认同。不少朋友会说:“到了国外仍然可以读唐诗啊,而且,别的国家也有很多好诗!” 因此,我必须对这件事情多说几句。 我心中的唐诗,是一种整体存在。存在于羌笛孤城里,存在于黄河白云间,存在于空山新雨后,存在于浔阳秋瑟中。只要粗通文墨的中国人一见相关的环境,就会立即释放出潜藏在心中的意象,把眼前的一切卷入诗境。 心中的意象是从很小的时候就潜藏下来的。也许是父母吟诵,也许是老师领读,反正是前辈教言中最美丽的一种。父母和老师只要以唐诗相授,也会自然地消除辈分界限,神情超逸地与晚辈一起走进天性天籁。 于是,唐诗对中国人而言,是一种全方位的美学唤醒:唤醒内心,唤醒山河,唤醒文化传代,唤醒生存本性。 而且,这种唤醒全然不是出于抽象概念,而是出于感性形象,出于具体细节。这种形象和细节经过时间的筛选,已成为一个庞大民族的集体敏感、通用话语。 有时在异国他乡也能见到类似于“月落乌啼”、“独钓寒江”那样的情景,让我们产生联想,但是,那种依附于整体审美文化的神秘诗境,却不存在。这就像在远方发现一所很像自己老家的小屋,或一位酷似自己祖母的老人,虽有一时的喜悦,但略加端详却深感失落。失落了什么?失落了与生命紧紧相连的全部呼应关系,失落了使自己成为自己的那份真实。 当然,无可替代并不等于美。但唐诗确实是一种大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一读,都能把心灵提升到清醇而又高迈的境界。回头一想,这种清醇、高迈本来就属于自己,或属于祖先秘传,只不过平时被大量琐事掩埋着。唐诗如玉杵叩扉,叮叮当当,嗡嗡喤喤,一下子把心扉打开了,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美好的自己。 这个自己,看似稀松平常,居然也能按照遥远的文字指引,完成最豪放的想象,最幽深的思念,最入微的观察,最精细的倾听,最仁爱的同情,最洒脱的超越。 这个自己,看似俗务缠身,居然也能与高山共俯仰,与白云同翻卷,与沧海齐阴晴。 这个自己,看似学历不高,居然也能跟上那么优雅的节奏,那么铿锵的音韵,那么华贵的文辞。 这样一个自己,不管在任何地方都会是稀有的,但由于唐诗,在中国却成了非常普及的常态存在。 正是这个原因,我才说,怎么也舍不得离开产生唐诗的土地,甚至愿意下辈子还投生中国。 我也算是一个走遍世界的人了,对国际间的文化信息并不陌生,当然知道处处有诗意,不会在这个问题上陷入狭隘民族主义的泥坑。但是正因为看得多了,我也有理由作出一个公平的判断:就像中国人在宗教音乐和现代舞蹈上远远比不上世界上有些民族一样,而唐诗,则是人类在古典诗歌领域的巍峨巅峰,很难找到可以与它比肩的对象。 二 很多文学史说到唐诗,首先都会以诗人和诗作的数量来证明,唐代是一个“诗的时代”。 这样说说也未尝不可,但应该明白,数量不是决定性因素。这正像,现在即使人人去唱“卡拉OK”,也不能证明这是一个音乐的时代。 若说数量,我们都知道的《全唐诗》收诗四万九千多首,包括作者两千八百余人。当然这不是唐代诗作的全部,而是历时一千年后直到清代还被保存着的唐诗,却仍然是蔚为大观。《全唐诗》由康熙皇帝写序,但到了乾隆皇帝,他一人写诗的数量已经与《全唐诗》差不多。因为除去他的《乐善堂全集》、《御制诗馀集》、《全韵诗》、《圆明园诗》之外,在《晚晴簃诗汇》中还说有四万一千八百首。如果加在一起,真会让一千年前的那两千八百多个作者羞愧了。只不过,如果看质量,乾隆能够拿得出哪一首来呢? 宽泛意义上的写诗作文,是天底下最容易的事,任何已经学会造句的人只要放得开,都能随手涂出一大堆。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经常看到当代很多繁忙的官员出版的诗文集,在字数、厚度和装帧上几乎都能超过世界名著,而且听说他们还在继续高产,劝也劝不住。这又让我想起了乾隆。他如此着魔般地写诗,满朝文武天天喝彩,后来终于有一位叫李慎修的官员大胆上奏,劝他不必以写诗来呈现自己的治国才能。乾隆一看,立即又冒出了一首绝句—— 慎修劝我莫为诗,我亦知诗不可为。 但是几馀清宴际,却将何事遣闲时? 对此,今人钱钟书讽刺道,李慎修本来是想拿一点什么东西去压压乾隆写诗的欲焰的,没想到不仅没有压住,连那东西也烧起来了,反而增加了一蓬火。 从这蓬火,我们也能看到乾隆的诗才了。但平心而论,诗才虽然不济,却也比现在很多官员的诗作清顺质朴一点。 说唐诗时提乾隆,好像完全不能对应,但这不能怪我。谁叫这位皇帝要以自己一个人的诗作数量来与《全唐诗》较量呢! 其实,唐诗是无法较量的,即便在宋代,在一些杰出诗人手中,也已经不能了。 这是因为,唐代诗坛有一股空前的大丈夫之风,连忧伤都是浩荡的,连曲折都是透彻的,连私情都是干爽的,连隐语都是靓丽的。这种气象,在唐之后再也没有完整出现,因此又是绝后的。 更重要的是,这种气象,被几位真正伟大的诗人承接并发挥了,成为一种人格,向历史散发着绵绵不绝的体温。 三 首先当然是李白。 李白永远让人感到惊讶。我过了很久才发现一个秘密,那就是,我们对他的惊讶,恰恰来自于他的惊讶,因此是一种惊讶的传递。他一生都在惊讶山水,惊讶人性,惊讶自己,这使他变得非常天真。正是这种惊讶的天真,或者说天真的惊讶,把大家深深感染了。 我们在他的诗里读到千古蜀道、九曲黄河、瀑布飞流时,还能读到他的眼神,几分惶恐,几分惊叹,几分不解,几分发呆。首先打动读者的,是这种眼神,而不是景物。然后随着他的眼神打量景物,才发现景物果然那么奇特。 其实,这时读者的眼神也已经发生变化,李白是专门来改造人们眼神的。历来真正的大诗人都是这样,说是影响人们的心灵,其实都从改造人们的感觉系统入手。先教会人们怎么看,怎么听,怎么发现,怎么联想,然后才有深层次的共鸣。当这种共鸣逝去之后,感觉系统却仍然存在。 这样一个李白,连人们的感觉系统也被他改造了,总会让大家感到亲切吧,其实却不。他拒绝人们对他的过于亲近,愿意在彼此之间保持一定程度的陌生。这也是他与一些写实主义诗人不同的地方。 李白给人的陌生感是整体性的。例如,他永远说不清楚自己的来处和去处,只让人相信,他一定来自谁也不知道的远处,一定会去谁也不知道的前方;他一定会看到谁也无法想象的景物,一定会产生了谁也无法想象的笔墨…… 他也写过“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样可以让任何人产生亲切感的诗句,但紧接着就产生了一个严峻的问题:既然如此思乡,为什么永远地不回家乡?他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拥有足够的自由,偶尔回乡并不是一件难事。但是,这位写下“中华第一思乡诗”的诗人执意要把自己放逐在异乡,甚至不让任何一个异乡真正亲切起来,稍有亲密就拔脚远行。原来,他的生命需要陌生,他的生命属于陌生。 为此,他如不系之舟,天天在追赶陌生,并在追赶中保持惊讶。但是,诗人毕竟与地理考察者不同,他又要把陌生融入身心,把他乡拥入怀抱。帮助他完成这种精神转化的第一要素,是酒。“人分千里外,兴在一杯中”,“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都道出了此间玄机。帮助他完成这种精神转化的第二要素,那就是诗了。 对于朋友,李白也是生中求熟、熟中求生的。作为一个永远的野行者,他当然很喜欢交朋友。在马背上见到迎面而来的路人,一眼看去好像说得上话,他已经握着马鞭拱手行礼了。如果谈得知心,又谈到了诗,那就成了兄弟,可以吃住不分家了。他与杜甫结交后甚至到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地步,可见一斑。 然而,与杜甫相比,他算不上一个最专情、最深挚的朋友。刚刚道别,他又要急急地与奇异的山水相融,并在那些山水间频频地马背拱手,招呼新的好兄弟了。他老是想寻仙问道,很难把友情作为稳定的目标。他会要求新结识的朋友陪他一起去拜访一个隐居的道士。发现道士已经去世,便打听下一个值得拜访对象,倒也并不要求朋友继续陪他。于是,又一番充满诗意的告别,云水依依,帆影渺渺。 历来总有人对他与杜甫的友情议论纷纷,认为杜甫写过很多怀念他的诗,而他则写得很少。也有人为此作出解释,认为他的诗失散太多,其中一定包括着很多怀念杜甫的诗。这是一种善良的愿望,而且也有可能确实是如此。但是,应该看到,强求他们在友情上的平衡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毕竟是相当不同的两种人。虽然不同,却并不影响他们在友情领域的同等高贵。 这就像大鹏和鸿雁相遇,一时间巨翅翻舞,山川共仰。但在它们分别之后,鸿雁不断地为这次相遇高鸣低吟,而大鹏则已经悠游于南溟北海,无牵无碍。差异如此之大,但它们都是长空伟翼、九天骄影。 四 李白与杜甫相遇,是在公元七四四年。那一年,李白四十三岁,杜甫三十二岁,相差十一岁。 很多年前我曾对这个年龄产生疑惑,因为从小读唐诗时一直觉得杜甫比李白年长。李白英姿勃发,充满天真,无法想象他的年老;而杜甫则温良醇厚,恂恂然一长者也,怎么可能是颠倒的年龄?由此可见,艺术风格所投射的生命基调,会在读者心目中兑换成不同的年龄形象。这种年龄形象,与实际年龄常常有重大差别。 事实上,李白不仅在实际年龄上比杜甫大十一岁,而且在诗坛辈分上整整先于杜甫一个时代。那就是,他们将分别代表安史之乱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唐朝。李白的佳作,在安史之乱以前大多已经写出,而杜甫的佳作,则主要产生于安史之乱之后。 这种隔着明显界碑的不同时间身份,使他们两人见面时有一种异样感。李白当时已名满天下,而杜甫还只是崭露头角。杜甫早就熟读过李白的很多名诗,此时一见真人,崇敬之情无以言表。一个取得巨大社会声誉的人往往会有一种别人无法模仿的轻松和洒脱,这种风范落在李白身上更是让他加倍地神采飞扬。眼前的杜甫恰恰是最能感受这种神采的,因此他一时全然着迷,被李白的诗化人格所裹卷。 李白见到杜甫也是眼睛一亮。他历来不太懂得识人,经常上当受骗,但那是在官场和市井。如果要他来识别一个诗人,他却很难看错。即便完全不认识,只要吟诵几首,交谈几句,便能立即作出判断。杜甫让他惊叹,因此很快成为好友。他当然不能预知,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将与他一起成为执掌华夏文明诗歌王国数千年的最高君主而无人能够觊觎;但他已感受到,无法阻挡的天才之风正扑面而来。 他们喝了几通酒就骑上了马,决定一起去打猎。 他们的出发地也就是他们的见面地,在今天河南省开封市东南部,旧地名叫陈留。到哪儿去打猎呢?向东,再向东,经过现在的杞县、睢县、宁陵、到达商丘,从商丘往北,直到今天的山东地界,当时有一个大泽湿地,这便是我们的两位稀世大诗人纵马打猎的地方。 当时与他们一起打猎的,还有一位著名诗人高适。高适比李白小三岁,属于同辈。这位能够写出“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这种慷慨佳句的诗人,当时正在这一带“混迹渔樵”,“狂歌草泽”。也就是说,他空怀壮志在社会最底层艰难谋生,无聊晃悠。我不知道他当时熟悉杜甫的程度,但一听到李白前来,一定兴奋万分。这是他的土地,沟沟壑壑都了然于心,由他来陪猎,再合适不过。 挤在他们三人身边的,还有一个年轻诗人,不太有名,叫贾至,比杜甫还小六岁,当时才二十六岁。年龄虽小,他倒是当地真正的主人,因为他在这片大泽湿地北边今天山东单县的地方当着县尉,张罗起来比较方便。为了他的这次张罗,我还特地读了他的诗集。写得还算可以,却缺少一股气,尤其和那天在他身旁的大诗人一比,就显得更平庸了。贾至还带了一些当地人来凑热闹,其中也有几个能写写诗。 于是,一支马队形成了。在我的想象中,走在最前面的是高适,他带路;接着是李白,他是马队的主角,由贾至陪着;稍稍靠后的是杜甫,他又经常跨前两步与李白并驾齐驱;贾至带来的那些人,跟在后面。 当时的那个大泽湿地,野生动物很多。他们没走多远就挽弓抽箭,扬鞭跃马,奔驰呼啸起来。高适和贾至还带来几只猎鹰,这时也像闪电般蹿入草丛。箭声响处,猎物倒地,大家齐声叫好,任何人的表情都不像此地沉默寡言的猎人,更像追逐嬉戏中的小孩。马队中,喊得最响的大多是李白,而骑术最好的应该是高适。 猎物不少,大家觉得在野地架上火烤着吃,最香最新鲜,但贾至说早已在城里备好了酒席。盛情难却,那就到城里去吧。到了酒席上,几杯下肚,诗就出来了。这是什么地方啊,即席吟诗的不是别人,居然是李白和杜甫,连高适也只能躲在一边了,真是奢侈之极。 近年来我频频去陈留、商丘、单县一带,每次都会在路边长久停留,设想着那些马蹄箭鸣,那些呼啸惊叫。中国古代大文豪留下生命踪迹的地方,一般总是太深切、太怨愁、太悲壮,那样的地方我们见得太多了。而在这里,只有单纯的快乐,只有游戏的勇敢,既不是边塞,也不是沙场,好像没有千年重访的理由,但是,我怀疑我们以前搞错了。 诗有典雅的面容,但它的内质却是生命力的勃发。无论是诗的个体、诗的群体、诗的时代都是这样。没有生命力的典雅,并不是我们喜欢的诗。因此,由诗人用马蹄写诗的旷野,实在可以看作被我们遗落已久的宏大课本。 诗人用马蹄写诗的地方也不少,但这儿,是李白、杜甫一起在写,这如何了得。 我曾动念,认认真真学会骑马,到那儿驰骋几天。那一带已经不是打猎的地方了,但是,总还可以高声呼啸吧?总还可以背诵他们的几首诗作吧? 在那次打猎活动中,高适长时间地与李白、杜甫在一起,并不断受到他们鼓舞,决定要改变一种活法。很快他就离开这一带游历去了。 李白和杜甫从秋天一直玩到冬天。分手后,第二年春天又在山东见面,高适也赶了过来。不久,又一次告别,又一次重逢,那已经是秋天了。当冬天即将来临的时候,李白和杜甫这两位大诗人永久地别离了。 当时他们都不知道这是永诀,李白在分别之际还写了“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的诗,但金樽再也没有开启。因此,这两大诗人的交往期,一共也只有一年多一点,中间还有不少时间不在一起。 世间很多最珍贵的友情都是这样,看起来亲密得天老地荒、海枯石烂了,细细一问却很少见面。相反,半辈子坐在一个办公室面对面的,很可能尚未踏进友谊的最外层门槛。 就在李白、杜甫别离的整整十年之后,安史之乱爆发。那时,李白已经五十四岁,杜甫四十三岁。他们和唐代,都青春不再。 仍然是土地、马蹄,马蹄、土地,但内容变了。 五 在巨大的政治乱局中,最痛苦的是百姓,最狼狈的是诗人。 诗人为什么最狼狈? 第一,因为他们敏感,满目疮痍使他们五内俱焚;第二,是因为他们自信,一见危难就想按照自己的逻辑采取行动;第三,是因为他们幼稚,不知道乱世逻辑和他们的心理逻辑全然不同,他们的行动不仅处处碰壁,而且显得可笑、可怜。 历来总有一些中国文人隔着灾祸大谈“乱世应对学”、“危局维持学”、“借故隐潜学”、“异己结盟学”、“逆境窥测学”、“败势翻盘学”,并把这一切说成是“中华谋略”、“生存智慧”。而且,因为世上总是苦恼的人多,失意的人多,无助的人多,这种谈论常常颇受欢迎,甚至轰动一时。但是,这一切对真正的诗人而言,毫无用处。他们听不懂,也不想听。这不是因为他们愚笨,而是因为他们在长期的诗人生涯中知道了人生的不同等级。降低了等级而察言观色、上下其手,打死他们也不会。 他们确实“不合时宜”,但是,也正因这样,才为人世间留下了超越一切“时宜”的灵魂,供不同时代的读者一次次贴近。 安史之乱爆发前夕,李白正往来于今天河南省的商丘和安徽省的宣城之间。商丘当时叫梁苑,李白结婚才四年的第三任妻子住在那里。安史之乱爆发时叛军攻击商丘,李白便带着妻子南下逃往宣城,后来又折向西南躲到江西庐山避祸。 李白是一个深明大义之人,对安禄山企图以血火争夺天下的叛乱行径十分痛恨。他祈望唐王朝能早日匡复,只恨自己不知如何出力。在那完全没有传媒、几乎没有通信的时代,李白在庐山的浓重云雾间焦虑万分。 当时的唐王朝,正在仓皇逃奔的荒路上。从西安逃往成都,半道上还出现了士兵哗变,唐玄宗被逼处死了杨贵妃。惊恐而又凄伤的唐玄宗已经很难料理政事,便对天下江山作了一个最简单的分派:指令儿子李亨守卫黄河流域,指令另一个儿子李璘守卫长江流域。李亨已经封为太子,李璘已被封为永王。李白躲藏的庐山,当然由李璘管辖。 李璘读过李白的诗,偶尔得知他的藏躲处,便三次派一个叫韦子春的人上山邀请他加入幕府。所谓幕府,就是军政大吏的府署,李璘是想让李白参政,担任政治顾问之类的角色。 李白早有建功立业之志,更何况在这社稷蒙难之时,当然一口答应。在他心目中,黄河流域已被叛军糟践,帮着永王李璘把长江流域守卫住,是当务之急。然后,还要打到黄河流域去,“誓欲清幽燕”、“不惜微躯捐”。 既然这样,立即下山就得了,为什么还要麻烦韦子春三度上山来请呢?这是因为,妻子不同意。李白的这位妻子姓宗,是武则天时的宰相宗楚客的孙女,很有政治头脑。在她心目中,那么有政治经验的祖父也会因为不小心参与了一场宫廷角逐而被处死,仕途实在是不可预测。她并不疑怀丈夫参政的正义性,但几年的夫妻生活已使她深知自己这位可爱的丈夫在政治问题上的弱点,那就是充满理想而缺少判断力,自视过高而缺少执行力。她所爱的,就是这么一位天天只会喝酒、写诗,却又幻想着能像管仲、晏婴、范蠡、张良那样辅弼朝廷的丈夫,如果丈夫一旦真的要把幻想坐实,非坏事不可。 为此,夫妻俩发生了争吵。拖延了一些时日,李白终于写了《别内赴征三首》,下山“赴征”,投奔李璘去了。但是,离家的情景他一直记得:“出门妻子强牵衣。” 事实很快证明,妻子的担忧并非多余。李白确实分辨不了复杂的政局。 李璘固然接受了父王唐玄宗的指令,但那个时候他的哥哥李亨,已经以太子的身份在灵武(在今天的宁夏)即位,成了唐肃宗,并把父亲唐玄宗尊为“太上皇”。悲悲戚戚的唐玄宗逃到了成都,他也是事后才获知从遥远的灵武传来的消息,并不得不接受的。这个局面,给李璘带来了大麻烦。他正遵照父王的指令为了平叛在襄阳、江夏一带招兵买马,并顺长江东下,到达江西九江(当时叫浔阳),准备继续东进。但是,他的哥哥李亨却传来旨令,要他把部队顺江西撤到成都,侍卫父亲。李璘没听李亨的,还是东下金陵。李亨认为这是弟弟蔑视自己刚刚取得的帝位,故意抗旨,因此安排军事力量逼近李璘,很快就打起来了。 这一打,引起了李璘手下将军们的警觉。大将季广琛对大家说,我们本来是为了保卫朝廷来与叛军作战的,怎么突然之间陷入了内战,居然与皇帝打了起来?这不成了另一种反叛?后代将怎么评价我们?大家一听,觉得有理,就纷纷脱离李璘,李璘的部队也就很快溃散。李璘本人,在逃亡中被擒杀。他的罪名,是反叛朝廷,图谋割据。 这一下,李白蒙了。他明明是来征讨叛军,怎么转眼就落入了另一支叛军?他明明是来辅佐唐王朝的至亲的,怎么转眼这个至亲变成了唐王朝的至仇? 军人们都作鸟兽散了,而李白还在。更要命的是,在李璘幕府中,他最著名,尽管他未必做过什么。 于是,大半个中国都知道,李白上了贼船。 按照中国人的一个不良心理习惯,越是有名的人出了事,越是能激发巨大的社会兴奋。不久,大家都认为李白该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所有的慷慨陈词者,以前全是李白迷。 李白只能狼狈出逃。逃到江西彭泽时被捕,押解到了九江的监狱。妻子赶到监狱,一见就抱头痛哭。李白觉得,自己最对不起的,是这位妻子。 唐肃宗下诏判李白流放夜郎(在今天的贵州)。公元七五七年寒冬,李白与妻子在浔阳江泣别。一年多以后,唐肃宗因关中大旱而发布赦令,李白也在被赦的范围中。 听到赦令时,李白正行经至夔州一带,欣喜莫名,立即转身搭船,东下江陵。他在船头上吟出了一首不知多少中国人都会随口背诵的诗——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快,快,快!赶快逃出连自己也完全没有弄明白的政治泥淖,去追赶失落已久的诗情。追赶诗情也就是追赶自我,那个曾经被九州所熟悉、被妻子抱住不放的自我,那个自以为找到了却反而失落了的自我。 这次回头追赶,有朝霞相送,有江流作证,有猿声鼓励,有万山让路,因此,负载得越来越沉重的生命之船,又重新变成了轻舟。 只不过,习习江风感受到了,这位站在船头上的男子,已经白发斑斑。这年他已经五十八岁,他能追赶到的生命,只有四年了。 在这之前,很多朋友都在思念他。而焦虑最深的,是两位老朋友。 第一位当然是杜甫。他听说朝廷在议论李白案件时出现过“世人皆欲杀”的舆论,后来又没有得到有关李白的音讯,便写了一首五律。诗的标题非常直白,叫做《不见》,自注“近无李白消息”。全诗如下: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 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第二位是高适。当初唐肃宗李亨下令向不听话的弟弟李璘用兵,其中一位接令的军官就是高适。那时正在李璘营帐中的李白,很快就知道了这个消息。 “高适?”十年前在大泽湿地打猎时的马蹄声,又响起在耳边。 高适当然更早知道,自己要去征伐的对象中,有一个竟然是李白。他已经在马背上苦恼了三天,担心什么时候在兵士们捆绑上来的一大群俘虏里,发现一张熟悉的脸,该怎么处理。 六 那么,杜甫自己又怎么样了呢? 安史之乱前夕,杜甫刚刚得到一个小小的官职,任务是看守兵甲器械、管理门禁钥匙。 让一个大诗人管兵器和门禁,实在是太委屈了,但我总觉得这件事有象征意义。上天似乎要让当时中国最敏感的神经系统来直接体验一下,赫赫唐王朝的兵器,如何对付不了动乱,巍巍长安城的门禁,如何阻挡不了叛军。 毕竟,公元八世纪中叶的长安太重要了,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都是这样。当时全世界的顶级繁华要走向衰落,无人能够阻挡,却总要找到具有足够资格的见证者。 最好的见证者当然是诗人。唐朝大,长安大,因此这个诗人也必须大。仿佛有冥冥中的安排,让杜甫,领到了那几串铜钥匙。 身在首都,又拿着那几串铜钥匙,当然要比千里之外的李白清醒得多。杜甫注视着天低云垂、冷风扑面的气象,知道会有大事发生。 叛军攻陷长安后,杜甫很快就知道了李亨在灵武即位的消息。唐玄宗的时代已经变成了唐肃宗的时代,作为大唐官员,他当然要去报到。因此,他逃出长安城,把家人安置在鄜州羌村,自己则投入漫漫荒原,远走灵武。 但是,叛军的马队追上了杜甫和其他出逃者,押回长安,被当作俘虏囚禁起来。这种囚禁毕竟与监狱不同,叛军也没有太多的力量严密看守,杜甫在八个月后趁着夏天来到,草木茂盛,找了一个机会在草木的掩蔽下逃出了金光门。这个时候他已听说,唐肃宗离开灵武到了凤翔。凤翔在长安西边,属于今天的陕西境内,比甘肃的灵武近得多了。杜甫就这样很快找到了流亡中的朝廷,见到了唐肃宗。唐肃宗只比杜甫大一岁,见到眼前这位大诗人脚穿麻鞋,两袖露肘,衣衫褴褛,有点感动,便留他在身边任谏官,叫“左拾遗”。 对此,杜甫很兴奋,就像李白在李璘幕府中的兴奋一样。 但是,不到一个月,杜甫就出事了。时间,是公元七五七年旧历五月。请注意,这也正是李白面临巨大危机的时候。 两位大诗人,同时在唐王朝两位公子手下遇到危机,只是性质不同罢了。杜甫遇到的麻烦,要比李白小一点,但同样,都是因为诗人不懂政事。 杜甫的事,与当时唐肃宗身边的一个显赫人物房琯有关。 房琯本是唐玄宗最重要的近臣之一,安史之乱发生时跟从唐玄宗从长安逃到四川,是他建议任命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来主持平叛并收复黄河流域的。后来李亨在灵武即位后,又由他把唐玄宗的传国玉玺送到灵武,因此,李亨很感念他,对他十分器重。叛军攻陷长安后,他自告奋勇选将督师反攻长安,却大败而归,让唐肃宗丢尽了脸面。此人平日喜欢高谈虚论,因此就有御史大夫贺兰进明等人趁机挑拨,说房琯只忠于唐玄宗,对唐肃宗有二心。这触到了唐肃宗心中的疑穴,便贬斥了房琯。 朝中又有人试图追查房琯的亲信,构陷了一个所谓“房党”。杜甫是认识房琯的,而所谓“房党”中更有一位曾与李白、杜甫、高适一起打猎的贾至。大家还记得,那时他在单县担任小小的县尉,才二十六岁,现在也快到四十岁了。那天大泽湿地间的青春马蹄,既牵连着今天东南方向李白和高适的对峙,又牵连着今天西北方向杜甫和贾至的委屈,当时奔驰呼啸着的四个诗人,哪里会预料到这种结果! 杜甫的麻烦来自他的善良,与司马迁当年遇到的麻烦一样,为突然被贬斥的人讲话。他上疏营救房琯,说房琯“少自树立,晚为醇儒,有大臣体”,希望皇上能“弃细录大”。唐肃宗正在气头上,听到这种教训式的话语,立即拉下脸来,要治罪杜甫,“交三司推问”。 这种涉及最高权力的事,一旦成了反面角色,总是凶多吉少。幸好杜甫平日给人的印象不错,新任的宰相张镐和御史大夫韦陟站出来替他说情,说“甫言虽狂,不失谏臣体”。意思是,谏臣就是提意见的嘛,虽然口出狂言,也放过他吧。唐肃宗一听也对,就叫杜甫离开职位,回家探亲,后来又几经曲折贬为华州司功参军。贾至被贬为汝州刺史,而房琯本人,则被贬为邠州刺史。 华州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华县。杜甫去时,只见到处鸟死鱼涸,满目蒿莱,觉得自己这么一个被贬的芥末小官面对眼前的景象完全束手无策。既然如此就不应该虚占其位,杜甫便弃官远走,带着家属到甘肃找熟人,结果饥寒交迫,又只得离开。他后来的经历,可以用他自己的一首诗句来概括:“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公元七七○年冬天,病死在洞庭湖的船中,终年五十八岁。 杜甫一生,几乎都在颠沛流离中度过。安史之乱之后的中国大地,被他看了个够。他与李白很不一样,李白常常意气扬扬地佩剑求仙,一路有人接济,而他则只能为了妻小温饱屈辱奔波,有的时候甚至像难民一样不知夜宿何处。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创造了一种稀世的伟大。 那就是,他为苍生大地投注了极大的关爱和同情。再小的村落,再穷的家庭,再苦的场面,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静静观看,细细倾听,长长叹息,默默流泪。他无钱无力,很难给予具体帮助,能给的帮助就是这些眼泪和随之而来的笔墨。 一种被郑州白癜风治疗中心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
|
当前位置: 月季花_月季花种类_月季花花语 >唐诗几男子
时间:2016-12-1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投放饵料鱼后桂花鱼死亡,疑为暴食后缺氧衰
- 下一篇文章: 慢寻店全国青年旅舍最全汇总出游在